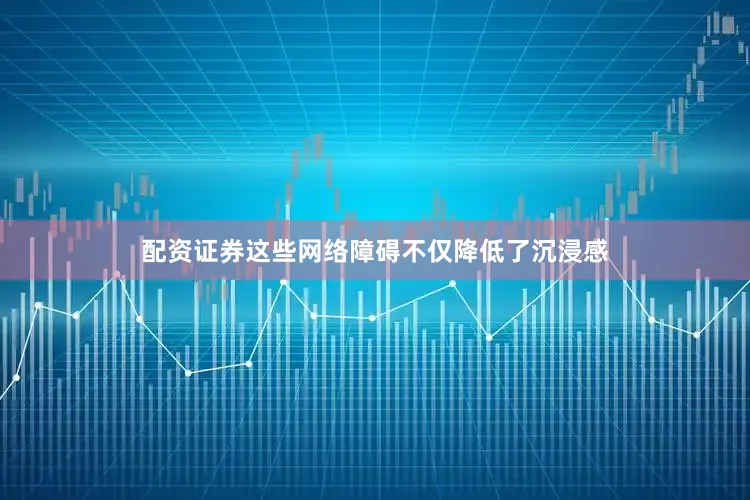1949年,国民党在战场节节败退,不少国民党将领都被我军俘获。可狡猾的李弥却硬是从我党手下逃了出去。

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?其实,逃跑途中,他也非常狼狈,甚至连唱戏都学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要论李弥的“滑”,还得从徐州撤退那会儿说起。
1948年底,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得像铁桶,老蒋急得在南京跳脚,催着徐州的杜聿明带着邱清泉、李弥、孙元良3个兵团南下救人。可华野的阻击阵地跟铜墙似的,3个兵团打了半个月,连对方的边都没摸着。
杜聿明没办法,跟蒋介石商讨了整整一宿,最终拍板下了决定:“撤!放弃徐州,保住这三个兵团再说。”

按计划,11月30号晚上统一行动,李弥的13兵团得留到最后,炸掉火车站、仓库这些要紧地方,给大部队打掩护。
可李弥哪会乖乖听指挥?30号中午,徐州城里突然“轰隆”一声,火车站那边冒起黑烟,爆炸声传出去几十里。华野的侦察兵在望远镜里瞅见这动静,一拍大腿:“不好,国军要跑!”
这边杜聿明还在指挥部里叮嘱“保密、保密”,那边李弥已经带着兵团部和第九军的人上了路。出发前他跟第九军军长周藩撇嘴:“让咱垫后?说白了就是让咱当垫背的。30万人挤一条路,走得动才怪。”
这话还真没说错。当天晚上杜聿明带着大部队撤退时,可算见识了什么叫“堵成一锅粥”。
卡车、大炮、马车挤在城门口,士兵们扛着枪踩着老乡的麦田往前钻,你推我搡乱成一团。杜聿明的指挥车卡在门缝里,司机急得满头汗,最后绕到城南才勉强挤出去,原定往西撤,愣是被挤得拐了向南的道。
出了城更糟,公路上全是人和车,军官骂着“让开”,士兵喊着”别挤”,辎重队的马受惊了,拖着炮车横冲直撞,一天下来才挪了20多里,连萧县的边都没摸着。

而李弥早带着人抄了北边的小路,溜溜达达走得轻快。为了怕杜聿明打电话来骂,他干脆让通讯兵把电台全关了,玩起了“失联”。等杜聿明的大部队磨磨蹭蹭到了萧县孟集,才撞见正蹲在老乡屋檐下烤火的李弥部队。本该垫后的人,居然跑到了最前头。
电话里杜聿明气得破口大骂,李弥就在那头嘿嘿笑:“杜总,不是我不等你,实在是部队太乱,我怕被冲散了……”挂了电话,他却转头跟手下说:“骂两句怕啥?命在,比啥都强。”
要是说徐州撤退是李弥的“开胃小菜”,那陈官庄突围就是他的“拿手好戏”。

1949年1月6号,华野的炮火把陈官庄炸成了火海。
李弥的13兵团阵地最先扛不住,青龙集那边的士兵喊着“跑啊”往后退,阵地像被啃过的饼,缺了一大块。到9号晚上,整个防线都垮了,杜聿明在指挥部里拍着桌子喊“突围”,声音都发颤。
乱哄哄的夜里,李弥却脑子清醒得很。他知道跟着大部队突围就是送死,几十万人往一个方向冲,解放军的机枪早架好了。他揣着个馒头,借着夜色溜到第9军3师的指挥所,找到师长周藩。

“周师长,咱不能就这么完了。”李弥往火堆里添了根柴,火苗映着他的脸,“你看这样行不行?你带着弟兄们跟对面谈谈,就说咱投降。”周藩愣了:“司令,咱真降?”“傻小子,”李弥踹了他一脚,“降是假的,让他们停火才是真的。等乱糟糟的时候,咱就溜。”
他还特意让警卫员找了件带血的士兵棉衣,往脸上抹了把锅底灰,佝偻着腰跟个伤兵似的。等到后半夜,周藩的人真跟解放军接上了头,双方正在清点人数,乱糟糟的人堆里,李弥趁着哨兵转身的功夫,猫着腰钻进了旁边的麦秸垛。
等他从垛子里钻出来,天快亮了。雪地里的脚印歪歪扭扭,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南走,怀里揣着半块冻硬的牛肉干,那是他突围前特意藏的。
走了没几里地,迎面撞见个解放军哨卡,两个战士端着枪问:“干什么的?”李弥赶紧低下头,操着一口云南腔:“老总,我是个书记官,部队打散了,想回家。”他故意把声音压得沙哑,棉袄上的血渍蹭到脸上,看着又冷又饿,活像个倒霉蛋。
战士又看了看他,没看出啥破绽,就挥挥手:“走吧,别乱晃悠。”他低着头快步走过,走出老远才敢回头,那哨卡的影子越来越小。

没走多久,路边蹲着个穿破军装的年轻人,正啃着冻红薯。李弥眼珠一转,凑过去递了块牛肉干:“兄弟,也迷路了?”原来,这年轻人叫汪新安,是被解放军放回家的国军士兵,见有人给吃的,赶紧接过来:“可不是嘛,从陈官庄跑出来的,家就在前边汪家庄。”
李弥边啃红薯边套话,听汪新安说他堂哥汪涛是当地保安团的团副,眼睛亮了。“我跟你回村歇歇?”他拍着汪新安的肩膀,“回头我给你找个好差事。”
汪新安哪见过这阵仗,揣着牛肉干就把他领回了村。见到汪涛时,李弥直接亮了身份,吓得汪涛手里的烟袋锅子掉在地上。“李司令?您……您咋在这儿?”“别叫司令,叫我老李。”李弥压低声音,“帮我出去,将来给你个营长当当。”
这话一出,汪涛的腰杆都直了。他连夜找来老表高大荣,三个人在炕头上合计:“从这儿到徐州,路上哨卡多,得装成走亲戚的。”

第二天一早,高大荣挑着个担子,李弥跟在后面,说是“串亲戚的表叔”。一路还算顺,1月16号就进了徐州城,住进汪涛的叔叔汪学思家。
可往南走就难了。城门查得严,没路条根本出不去。李弥蹲在院里琢磨半天,一拍大腿:“咱往北走!”汪学思吓了一跳:“往北是解放区啊!”“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”李弥嘿嘿笑,“他们准以为我往南跑,北边反倒松。”
找路条费了不少劲,汪学思托了个在伪保长家做饭的亲戚,才算弄来一张去潍县的路条。李弥揣着路条,跟着高大荣混上了往北的马车,车轱辘碾着冻硬的土路,他就裹着棉被缩在角落。
到了潍县,李弥想起个熟人:福聚祥饭庄的老板李惠之。当年他路过潍县,在饭庄吃过一顿,李惠之见他是个军官,鞍前马后伺候得周到。晚上他摸到饭庄后门,敲了三下。李惠之探出头,看清是他,差点喊出声,“我的娘,李司令,您咋来了?”
“嘘,”李弥捂住他的嘴,“借你这儿躲躲,将来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李惠之犹豫了半天,还是把他领进后院。“城里查得紧,你这模样太扎眼。”他瞅着李弥,“我有个侄子叫王桂和,是唱梆子的,走乡串镇没人管,你跟着他混?”

李弥咬咬牙:“行,唱戏就唱戏。”接下来3天,潍县饭庄的后院天天传出“咿咿呀呀”的唱腔。李弥跟着王桂和学身段,学甩袖子,嗓子本来就哑,唱出来跟破锣似的。王桂和急得不得了:“叔,您这不是唱戏,是哭丧啊!”
“能糊弄过去就行。”李弥抹了把汗,对着镜子练皱眉、弓腰,把自己往“落魄戏子”的模样上靠。
几天后,两人就扮成“叔侄俩”上了路。王桂和挑着戏箱,李弥跟在后面,遇到哨卡就说“去乡下赶场子”。有回哨兵让他唱两句,他憋了半天,哼了段云南小调,居然蒙混过关了。哨兵哪知道,这“戏子”前阵子还是个兵团司令。
快到青岛的时候,查得越来越严。王桂和就找了个运粮的老乡,塞了块银元,让李弥钻进装粮食的麻袋。麻袋里又闷又热,他憋得满头汗,听着外面哨兵的脚步声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直到马车进了青岛地界,他才被拽出来,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。

1949年2月,李弥站在青岛的码头上,看着远处的轮船笑了。后来蒋介石又把他派到云南。结果卢汉起义,把他堵在五华山。

这次他没跑,反倒假意写劝降信,转头就让部队炮轰昆明,城里的老百姓倒了霉,房子塌了一大片。等第8军在滇南被打垮,他又拍拍屁股溜到缅北。
在这里,他更是肆无忌惮,当地的人民苦不堪言。1954年,美军撤兵,蒋介石也趁机收了他的兵权。后来李弥就回台湾租了个小院子。1973年,李弥在台北病死,活了71岁。
李弥的种种罪行,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不小的灾难,我们也应该从他身上汲取教训,坚决反对任何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。
股票配资导航,股票交流平台,杠杆配资哪家好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配资查询网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
- 下一篇:炒股如何配资在复国运动陷入绝境之际